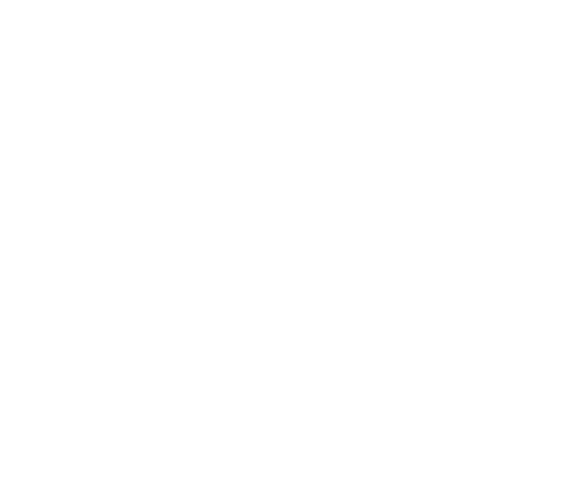“我不要这样的命,我要更好的自己”
第一次见到汪艾韬是在两年前。他个头小,迈着内八字,摇摇晃晃地走来。看到记者后,他立刻停下,将一只手甩起,在空中不规则地晃动,同时从嘴里咬出两个字:“你……好。” ️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线,露出一排牙齿,这是他出现频率最高的表情。
从出生开始,汪艾韬似乎就在不断经历各种大大小小的打破与接纳。他4岁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,又用接下来的16年,觉察并试图打破人们对脑瘫患儿的固有印象。如今, ️他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试图强迫自己表现得更“正常”一些,而是承认“脑瘫”的先天症状,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。
在汪艾韬看来,这是自己最大的成长,“我不想要这样的命,但我想要一个更好的我。”
汪艾韬(右一)在表演魔术
️从可能一生都要坐轮椅,️到站起来了
“自幼罹患脑瘫的我,在平路上行走就像在暴雨中攀登山路,坦途在脚下变得崎岖,脚底仿佛沾了泥渍、蹚了水流,步履左冲右撞。”
2002年9月,汪艾韬在安徽出生。一生下来,他就与别的婴儿不一样: ️他不会哭,不会吸奶,也一直学不会走路。
在浙江台州打工的父母带着他跑遍了当地医院,问诊结果都是发育不良、骨质疏松或缺钙。直到1岁7个月时,浙江省人民医院给出了脑瘫的最终诊断,同时也给汪艾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:如果在一岁半之前确诊,做一些治疗,脑瘫还有痊愈的可能,而误诊让他错过了这样的时机,只能通过康复训练去缓解症状。
“他可能一生都要坐轮椅。”医生这样告诉妈妈艾永雅。
最开始在医院的康复治疗并不顺利。艾永雅带着汪艾韬跑上海、去郑州,每次住院一般都要半年以上。这期间,让汪艾韬疼得忘不了的一个康复动作,是他躺在地上被按住,两个人要从左右把他的双腿拉到180度。
艾永雅回忆,儿子喜欢看书和动漫,扎针灸时,汪艾韬的脑袋像个刺猬,要留针几个小时,母子俩就一起看《爱探险的朵拉》。汪艾韬会跟着朵拉说:“backpack、monkey……”朵拉说跺跺脚,他也高兴地试着抬起一只脚。
除了吃饭和睡觉,训练几乎不中断。房间里铺满了软垫,汪艾韬的手臂被艾永雅拉拽着,在垫子上爬行。后来他自己爬,身体的动作像在水里狗刨,从房间的一头到另一头,从慢到快,从不断地停顿喘息到逐渐流畅。训练站立的时间也从10分钟增加到30分钟。
为了让训练中的汪艾韬可以放松,艾永雅在房间里放了一台DVD机,里面循环播放着海洋生物的纪录片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雨天的傍晚。汪艾韬爬累了,趴在地上睡去,艾永雅帮他盖好被子,转身离开去煮饭。房间里黑着灯,雨点砸在窗上,汪艾韬怵然惊醒,翻过身左右望,却找不到妈妈。他哭了,浑身颤抖。“我侧抬头,看到远处房间尽头DVD里的蓝色海底, ️像被一股力量牵引着,拉起身体,用两只手使劲撑住地面,眼睛死死盯着那片海,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”汪艾韬说。
汪艾韬试图行走去拉门把手,还没走到,门被打开了,门外愣住的艾永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:“你站起来了!”
小时候的汪艾韬和妈妈的合影
️“孤独只是人生路上
️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而已”
“在餐厅吃河蚌时,从蚌肉里掉落了一颗珍珠。或许我们在生活的熬煎与撕扯中,都曾被情绪的沙砾磨得鲜血淋漓,又把一切紧紧包裹在内心。”
到了上学的年龄,汪艾韬遇到的第一座山是写字。
汪艾韬在书写上需要比普通人花更多的力气。 ️刚开始练习时,汪艾韬每写一笔都要双脚离地,左手使劲抓住书桌边角,嘴巴张大,吐着粗气,用尽力气,却仍写不正横竖,字也写不到方格里。
为了练习,从一年级开始汪艾韬就被妈妈要求写日记,他的本子被妈妈不知撕过多少次,艾永雅回忆:“那时候,他哭,我也跟着哭。”
到了初中,班主任王静明白常规课堂和作业并不适合汪艾韬,所以他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在家自学,作业可以口述给妈妈听。
自学的方式由初中持续到高中,汪艾韬对校园的更多记忆集中在回去考试上。每次,他会被安排到一个提前准备好的单独考场,考试开始后,老师会把门反锁,他一个人在里面答卷。 ️汪艾韬考试需要延长时间,有时考完天已经黑了,别的学生已经在上晚自习,他一个人走回家。
临近高考时,汪艾韬会被妈妈关在小屋里一个人做题。作为文科生,他需要高强度的书写才能应对考试。为了适应这样的节奏,他会限定时长,严格按两小时的时间进行模拟。不止一次,妈妈进来探视时,发现纸上留下了摩擦渗出的血迹。
学累了,汪艾韬会到楼下的四角亭坐一会儿,他在小区没有什么朋友,看着眼前玩闹的孩子,汪艾韬感觉到了孤独,“越到后来,就越不想去那个亭子了。”
对于汪艾韬来说, ️“孤独只是人生路上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而已。”也是从那时开始,文学和戏剧成了他的倾诉对象和情感载体。
在中考和高考的考场上,汪艾韬都经历了胳膊痉挛。高考最后一场英语,痉挛让他的笔已经难以碰到纸面。在最后的半小时里,汪艾韬趴在桌子上,握紧了手中的笔。“我想起了那天死死盯着那片海站起的自己。医生说,我的余生只能坐轮椅。而如今,我已经能行走,何况手里还有这根‘登山杖’。”
️2025年,汪艾韬以603分的成绩考入暨南大学攻读戏剧编导专业。后来成为汪艾韬大学辅导员的安姗姗也喜欢他的文章和戏剧作品。在老师眼中,汪艾韬是一个很有“生命力”的学生,能够“沉得下去”,对一些领域和社会现象有深度思考。“他是会影响人的那种人。” 安姗姗说。
️希望自己的魔术
️能帮大家️找到“为此而活”的东西
“我想任何艺术都是对人类的‘可能性限制’的解构,用共鸣和爱砸碎一堵堵墙。魔术或许是我选择的方式,它隐喻着我的某种自我缝合。”
在前18年的人生中,汪艾韬的目标只有好好学习。他成绩名列前茅,写的诗歌和作文经常获得市级以上的奖项, ️“我对成绩的执念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的身体,我会很努力地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‘傻子’。”
或许正因为如此,他高三时陷入迷茫,自我接受的教育没有告诉他“好好学习”的原因,压力、迷茫与孤独挤压着汪艾韬。甚至在某一时刻,他看着飞驰而过的车辆,有一头冲进车流里的冲动,他意识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。汪艾韬这样写道:“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条路上跑下去。”
从小到大,汪艾韬都被告知,作为一个残疾人的正确生活方式就是好好读书,成为一个战胜一切困难的人,包括妈妈给他找的人生偶像,是考上哈佛、北大的残疾人榜样,但汪艾韬更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。
魔术是汪艾韬从小的爱好,他所在的小县城有一家魔术店,他经常哭着求妈妈带他去,在店里从下午待到天黑,跟着老板变各种魔术。 ️“我想做魔术师”,他无数次跟老板这样说。
变化出现在高三的一个夜晚,他上网看了一场英国剧场的魔术表演。与以往的魔术不同,舞台上的魔术师可以猜出观众心里的想法,帮助人们解答困惑。“希望我的表演,能够帮助大家找到‘为此而活’的东西。”魔术师在最后这样向观众谢幕。后来汪艾韬得知,这叫心灵魔术。
原来魔术是可以直接帮助别人的,“这才是有意义的事。”
这场心灵魔术成为了一个触发点,让汪艾韬寻找“为此而活”的力量——用艺术帮助他人。他报名了艺考,学习戏剧编导。艺考结束之后,他的抑郁症状自然愈合。
艺术的帮助不仅作用于他人,也包括自己。
️大二时,汪艾韬登上广东高校魔术协会的剧场舞台,用自己的原创方法呈现了经典的魔术效果——“巴格拉斯效果”。汪艾韬形容那是魔术圈内的“哥德巴赫猜想”,自己就像“一个演员去表演一段莎士比亚”,凭借抑郁症期间习得的心理学经验,运用 “正念”概念,让观众从心理上相信并将它投射到现实,他最终完成“巴格拉斯效果”。
汪艾韬在学校表演魔术
这是汪艾韬第一次独立完成一场魔术。当时在场的很多职业魔术师和爱好者,都没看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。这场魔术被发表在中国系列魔术大会线上讲座的讲义里,也让汪艾韬在广东魔术圈里积累了名气。
大三的时候,汪艾韬成为世界魔术大会(FISM)参赛选手张津铭的艺术顾问,并在9个月的时间里帮助他一起完成了创作。汪艾韬对FISM的心驰神往由来已久,初中时他就经常听魔术店老板讲世界魔术大会的神奇故事,但他始终怀疑,“病弱又渺小的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去现场感受。”
当那一天到来,张津铭走上舞台,喊出“Hello,FISMAsia”的瞬间,站在控音台俯瞰会场的汪艾韬瞬间泪目。“我不知道初中的我能不能听到……津铭做到了,我们做到了,我做到了。”
️“我不要这样的命,️我要更好的自己”
“我不可能治好自己,所以这个疗程会一直持续下去,成为我话语里的一部分,融入我,撕裂我,解构我,拼凑我。”
从出生开始,汪艾韬与妈妈艾永雅就被捆绑在一起。妈妈是课程老师、康复教练、保姆、司机……事无巨细,片刻不离。高考之后,艾永雅随汪艾韬一起来到广州,住进学校的公寓,他们面对的第一个课题变成了如何相互独立起来。
艾永雅来广州做过好几份工作,包括家教和商场员工。她每天6点起床,上早班,从不请假迟到。汪艾韬说:“现在我的生活基本上不需要妈妈照顾。”两人逐渐有了自己的空间。
汪艾韬和朋友在一起
汪艾韬忙于学业,去年9月被成功保研至本校读艺术学。他评价自己是“一个很要强的人”。在大学评选“自强之星”的答辩现场,工作人员询问汪艾韬是否需要一张椅子,以便坐着完成答辩。汪艾韬摇了摇头:“我还是想以站立的姿态完成。”
辅导员安姗姗还提到一次艺术展演的录制,汪艾韬兼任编剧、导演和主角。他对自己的表现特别较真,录制从下午5点持续到晚上近12点,一位协助录制的学生觉得已经可以收工了,汪艾韬坚持还要再来一条。
但现在的汪艾韬不再“逞强”。 ️从小到大,汪艾韬的“逞强”和很多脑瘫患儿一样,都源于“我想表现得正常一点”。在意识到自己身体“不正常”后,他曾一直努力把自己伪装得“正常”。
初一的时候,汪艾韬坚持在雨天自己打伞回家,结果手臂痉挛,伞无法拿稳,伞骨反复磕到他的头上,回到家时,已满头是血。汪艾韬和身体正常的朋友一起行走时,累了也不想落后。他把这一转变归因于学习艺术的影响。他最大的痛苦之一便是外界对于自己可能性的局限,而艺术带给他一种开放性。
汪艾韬和朋友的魔术戏剧作品《一半》就是一个例子。作为表演的一部分,他们和观众一起演绎自身的“一半”与“另一半”。他这样解释:在现实的一半里,一个像我这样有疾病的孩子能够走上舞台,能够表演,能够不追求“安稳规矩”的生活方式,这件事情依然被怀疑,因为大家太喜欢去铸造“可能性”的高墙。但是很幸运,在艺术的那一半里,魔术动摇和解构了可能性的限制,有了这“一半”,我自由且幸福。
去年12月,汪艾韬第一次被朋友“塞”上了轮椅,推进了“嗨吧”—— 一个他认为这辈子都不会踏足的地方。 ️朋友鼓励他:“坐在轮椅上,也可以跳舞。”在音乐声中,他被人拉着手转圈,真的跳起了舞。
汪艾韬在朋友圈写道:“命运欠我和你(妈妈)一句对不起……命运对不起我们,但是我们活得,足够对得起这个世界、这个命。 ️我愿意走下去,不是因为我想要这样的命,而是我想要一个更好的我。”
采写 | 邓蔚楠
统筹 | 宋建华
编选 | 石佳
监制 | 王子轩